评《凉宫春日的忧郁》——成人之美
更新时间:2025-10-09 11:47:11

作者/Flux
排版/两只青蛙跳下锅
封面/喵刀
“漫无止境的八月”,描述了暑假最后两周一万五千余次循环的异常状态。原属《凉宫春日的暴走》中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小章节,却成为了09版《凉宫》中最重要的追加内容。相较于书中仅对最后一次轮回进行详细刻画,动画以选取其中的八次进行影像化呈现。正因如此,几近相同的故事以每周一集的放送量反复播出了八次,这一章节引发了诸多争议,或者说是相当多的差评。
在09版《凉宫》播出16年后的今天,“八月篇”的价值已得到一定的重估——尽管很大程度上出于次年剧场版《消失》的成功。“要让观众也体会长门有希的心情。”因而便有了一对基于“量的不对等”之附着关系,即长门有希在595年的观测、忍受后,依然为阿虚留下一个重置的回车键,倘若大萌神如此,那么观众亦只好说服自己勉强接受后启《消失》的“八月篇”。

的确,漫无止境的八月,始终在平淡的日常漩涡中周旋,时间被无限拉长,使观众被置于快感的延迟享用中。有别于传统叙事中将观看时间视为透明媒介或通往故事内容的无形通道,“八月篇”刻意放大观看时间的重要性,使观看时间本身成为表达的载体,让观众具身化地感受到长门有希所承受的漫长轮回的重量。
埃里克.侯麦的《绿光》同样是一部关于“等待”的伟大作品。本片用一百分钟描绘了一位平凡女子“无事发生”的漂泊状态:Delphine寻求与他人相遇,她对自己的境遇不太满足,她在假期前夕连续两次被抛弃,因而陷入一种相当偶然的孤独中——这与侯麦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那种长期的、构成性的孤独不太一样(譬如《午后之爱》中的弗雷德里克,他游移的目光正面昭示了其被欲望束缚的分裂身体)。面对这份不期而至的孤独,Delphine展现出某种独特的应对逻辑。她表面上遵循朋友们务实的劝诫——应当适应生活,主动与人交往,或许还能在未知中邂逅爱情。然而出于更深层的本能,却婉拒着这种应对孤独的常规路径。在邂逅最终与她亲历绿光的男子Jacques之前,Delphine也几乎未曾让自己处于一种与对方不太和谐的尴尬境地,然而她却一次又一次地选择迅速撤离——悖论式的,她同时在接近又远离自己声称渴望的东西。她似乎缺乏一些促使自己收获满足的习惯,由于缺乏“习惯”,那些被称为“偶然”的事物势必被发展成仿佛无休无止的“必然”——那么倘若……存在一种潜在?
当苹果尚未坠落,引力法则不过是一个待现实化的假设。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倘若”,都在现实与潜在之间划出一道裂隙。自然法则以条件式呈现自身,而真正孕育变革之可能则永远栖息在“倘若”一词生成的褶皱中。
谈论可能性,就是着眼潜在。事物之倾向——可燃性、可溶性、柔韧性——指向的不是作为既成现实的某种属性或质态,而是单一实体在其无限的属性中被微分,并在其存在过程中进一步分化。所有事物都于潜在维度中普遍连接和交织延伸,等待着现实化,却又绝不同一于现实化。一根未被点燃的火柴依然保有燃烧的潜在性,说火柴可燃,也许同称之为不可燃一样,都是一种可能性的陈述。如果说一个物体可燃,那么意味着它在环境合适时总是燃烧;那么对于那些不可燃的物体,只需假设它们从未处于一个合适的环境中。或许,所有物体都是可燃的。
《绿光》中Delphine的徘徊与折返,恰如一根在空气中微微颤动、却又仍未与磷面发生接触的火柴。她并非无法点燃,而是对燃烧之样态有着近乎偏执的敏感。这种敏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即不是培养习惯来驯服偶然,而是悬置习惯来保持对偶然的绝对开放。Delphine本能地抗拒通过重复接触来交往更多的他人,身体倾斜程度发生改变时她心生排斥,仿佛不愿走近那扇门。她的举动令观众不适,恰恰是因为她罕见地被放逐出自然习惯的日常,在兼具威胁与活力的行走中陷入僵局;然而她从故事一开始便已经意识到:她必须找到自己生命中的那个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她渴望的是爱得以成为奇迹的那个瞬间。尽管就剧作层面而言,观众势必知晓片尾会出现绿光;但只有“奇迹”发生的那一刻,观众方能体会到整起事件的真正范畴:Delphine的渴望与不安、燥热同拉锯,都是在为最后的“Oui”做准备,在那一瞬间这名女子明了自己已完成使命。
关于最后的奇迹,听说侯麦将影片耗资最大的一笔费用花在了前往加那利群岛,希望实地捕捉那道光发生的瞬间。即便在生活中从未有幸见得绿光,但至少在视觉层面,我认为Delphine见到的这个物质并不十分美观;除此之外,在片尾卡司表出来前的海面有个很打眼的剪辑点,配乐也显然不是那种高扬的旋律,甚至有些诡异感。以上种种很难说是年代技术受限,或是作者本人剪辑水平/音乐品味不行如何如何。侯麦本人的意图大抵是,倘若能接受“奇迹”本身也只是一个常规名词,那么即便崇高裹挟着不堪,圣洁之物不那么美观,倒也不必因旋律失协而顿感被宇宙抛弃。

说回《凉宫》,该系列两大基本设定:一是春日可以影响世界的运行,二是春日的举动很大程度上受男主(阿虚,或者说是三年前的John Smith)的影响。“漫无止境的八月”,因春日暗自遗憾期待落空而发动,循环的终结却不依赖神明的自觉被打破。在这场叙事实验的外表下,可以窥见作为最纯粹梦游者的少女内心强烈的信念感——并非源于对世界的清醒认知,而是蕴藏于无意识的深处。当她略带嗔怒地接纳了阿虚那微不足道的邀约时,那个因执念所构筑的、凝固的“永恒”,悄然让渡于一个重归日常的当下。
八月篇的第四话中,两组看似并不相干的画面形成了有趣的互文。一个是阿虚数次仰望积雨云及模型飞机的场景;另一个则是春日用望远镜观测星空的画面。二者怀着迥然不同的心情望向远方之景。


阿虚所仰望的积雨云,庞大、洁白、充满变化,是夏日天空中最具时间性的造物,它预示着雷雨与天气的转变,本身即是“变化”的纹章;而模型飞机,则是人类对“远方”的微小模拟,它凭借人力放飞,却企图挣脱引力的束缚,划破天际。这两个意象,共同构筑了日常中的远景——存在于日常的背景中,却时时刻刻指向“别处”,一个不同于“此时此地”的潜在空间。它们标志着一种在重复内部生成的差异点,作为强度性的符号承载着逃离此在的欲望强度,在每一次循环中都积累着微小的差异。尽管阿虚渴望突破,但他的想象力始终被限制在由春日无意识所设定的物理与时空边界之内。所望之“彼岸”,仅仅是此岸的一个函数,是内部的一个出口标记,而非真正的外部。他的视线中,混杂着对自由的向往、对现状的疲惫,以及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为他所注目的,只是一个无法触及的符号,而非一个可以抵达的目的地。作为远景的日常,其功能不是被抵达,而是被持续地渴望。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春日通过望远镜对星空的凝视。望远镜,这样一台精密科学仪器,将春日的意识与宇宙的直接关联具象化,在寻找外部世界差异的同时,也暗示了她对自身无限潜在的确信。她所驻足的,不是此世内部易变的、充满水汽的云,而是此世之外、那些遵循着严格物理法则、在数百万光年外兀自闪耀的星云。星空作为背景中的被观测物,轮廓显得模糊,质感与蓝天白云不甚相似。这种视觉处理,无形中暗示了春日与这个她所创造的“世界”之间一种本质性的疏离。渴望欢乐时光永驻的野望直抵此世之外的远方——在体验世界,亦或是在检视她的造物?

一面是构筑于接续的现在基础上之时间,在重复内部寻找出口的容受性:当下的循环已然成为一种绵延。因而即便只是抬头仰望这一小小时刻,亦能延展为包裹所有时间的宇宙当下。一种更为庞大的当下收编了现在当下,过去同未来只是“当下”的相对区分,也仅仅是庞大当下的一部分,然而它也同样被宇宙当下所包裹。所以尽管积雨云预示着变化,但此处的变化,仅仅是天气系统内部的相变,是从一种稳定状态转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过渡。另一面是配置了诸事件之时间,具有创造重复本身的发生性:延展的当下在细分为过去同将来这两部分的过程中消失了。不存在任何可以被称为真正的当下之事件——它们要么已经发生,要么尚未来临。作为诸事件的时间与诸事件并不分离,当下并非一段曾经真正存在过的时间。所以对外部的驻足观测并非面向具体,以“诸事件的时间”去达成“非事件”的偏执延长了燥热的拉锯。
那么,“破局”是如何发生的?并非仰仗积雨云或是星辰的指引,而恰恰是目光被主动从远景中收回,汇聚于咖啡屋的小小空间内。阿虚与春日四目相对之时,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体验在粘稠的空气中悄然交织,创造出一种既非日常也非异常的全新空间——在上万次循环中积累的对于微小差异的感知,已自觉到潜在现实化的唯一必然性。

没有铺垫、没有预兆、也没有多余的客套。当春日捕捉到阿虚意图的瞬间,这场持续了一万五千余次的循环就突然被打破了。春日以她一贯的傲娇接受了邀约:咄咄逼人的嗔怒下,夹杂着些许几乎难以察觉的释然。她依然是那个能够改变世界基本法则的存在,却在有些口嫌体正直的行动中,逐渐理解并接纳了世界的本来样貌。她依然凝视着彼岸的星空,却同时学会了欣赏此岸的风景。你不觉得凉宫同学渐渐学会了有常识地玩耍吗?

在无尽的难以调和的漩涡中,留心春日既作神明亦为少女之暧昧的模糊性:“慌不择策”恰恰通过了此析取性综合的考验——并非着眼某种长远胜利的正面对抗或沉溺于人际日常的默然静观;不是春日自身的全貌,而是她存在于世的一个切面,一个即将跃入我们视觉盲区的残影。之所以“模糊不清”,正是因为它处于“在场”与“缺席”的临界点上。春日作为资讯唯物、意识唯心、量子时间三重世界观彼此互不取消的象征,其纯粹的、自我指涉的欲望(对永恒夏日的执着)正在从阿虚(这样同观众一般唯一的“普通人”)的视域中撤退。她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清晰审视、被分析解决的“问题”,而是重新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即将隐没于自身所创造的世界的“背景”之中。阿虚所感受到的,不是神明的正面宣示,而是少女转身离去时,大门敞开送来的热浪。这阵热浪,向凡人们宣告了任何试图从内部“解决”神明意志的企图的终结。面前这个闪烁的背影,意味着阿虚长久以来试图“看清”、进而“纠正”春日的幻想之破灭,其所蕴含着的循环之恐怖啮噬着注视者的内心,“试着向前迈一步”作为一种伦理性的动作,彰显了愿意更近漩涡的勇气,对逃逸之义无反顾的跃迁缔造出一个轻盈的新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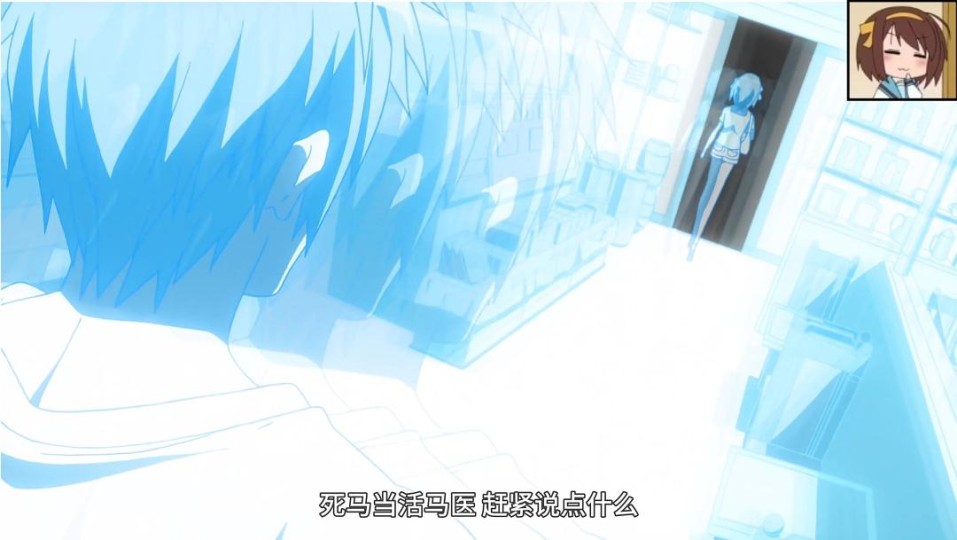
假使说“试着向前迈一步”意味着循环的终结,继而诱发《消失》中世界线的变革,那么以《Someday in the Rain》作为09版《凉宫》的完结则称得上是种美德。本集是动画版唯一不基于轻小说原著的原创集,脚本出自作者谷川流之手。作为这部伟大作品的收官,它彻底拒绝了任何形式的剧情高潮。没有冲突,没有告白,没有谜团揭晓,甚至春日本人的戏份都很少(长门很有画面可她没有一句台词)。当叙事停滞,纯粹的时间便浮现出来。期间那颗近200秒的长门独自看书的长镜头邀请观众以第三人称视角观看没有阿虚的世界,感受自身对时间——对同SOS团一起度过之时间的绵长思绪。雨中的某天,这间并不宽敞的活动室内,流淌着一种向日常动作演变的时间:所有的事件,同生命生成之记忆的时间。

正因如此,假使某天,聚焦这间活动室的人们都“觉得凉宫同学渐渐学会了有常识地玩耍”,那么她势必将少一些像六年级时看棒球比赛那样的困惑,而这几乎也象征着女孩正趋于普通。然而在不可逆自然规律作用下,她必然长大——事实上,我们难道不是一直在见证凉宫春日的成长嘛?我们欣喜于她的成长——纵使未曾得见她成人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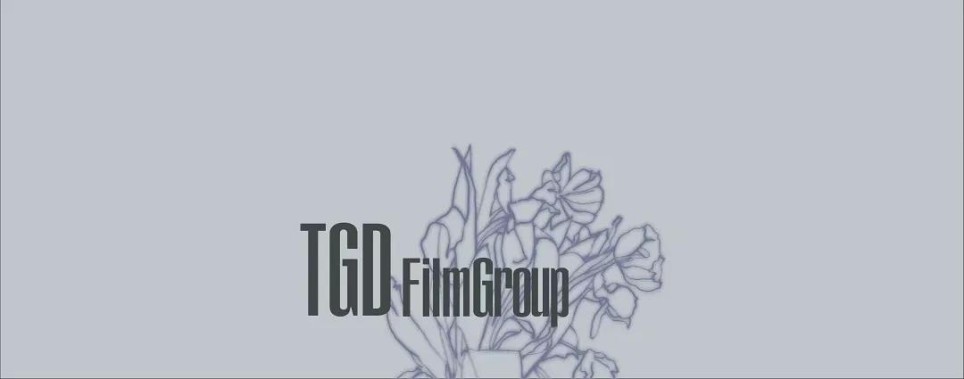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下一篇:这个故事不怎么可口
『凉宫春日的忧郁』相关阅读
 评《凉宫春日的忧郁》——成人之美
评《凉宫春日的忧郁》——成人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