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虚实的分析(长文,4500字)
更新时间:2025-08-25 13:38:24
原文链接【影/《敌》:生命的尽头,逃不过老残零落】
电影中很多虚实难辨的镜头,正是男主恍惚的精神状态写照。从男主的角度,现实、梦境与幻想,时刻交错,令他困惑。但从观影的角度,导演的镜头还是会注意交代下周围场景,让观众确认现实、梦境与幻想的界限。
////
电影的结构分为整齐的四段:夏—秋—冬—春。
夏
夏的部分交代了男主的生平和身份。他曾经是一位大学教授,专业方向是法国文学。现在的他,老年独居。每天的生活按部就班、波澜不惊。做饭、吃饭、敲敲电脑,写作、写遗书。丧妻无子嗣的他,人际关系十分简单,只是偶尔有人登门拜访。一般是他过去的学生。偶尔也会有人邀请他参加社会活动,比如去做关于法国文学的演讲。但他的开价又劝退了不少邀请者。不是他不缺钱,而是他坚守自己的演讲底线不降价。
夏的最后一个场景是他的一个女学生过来看望他。在晚饭的时候,她很是暧昧地对老师说,她要离婚了。

秋
秋的部分是电影的转折。秋意味着一切开始凋零。
在这个段落里,女学生并没有真的出现,但出现在了他的梦中。梦里,他们俩还是愉快地在家里共进晚餐。女学生要赶最后一班车回家,让他抓住最后一刻与她欢愉的机会。梦中的他有些火急火燎,然后就醒了。醒来的他趴在沙发上。他慌忙检查了自己的下半身,其实连裤腰带都没有松。他又看了看桌子,结果只有一个人的餐碟。
这不是他第一次做“奇怪的”梦。在这个梦之前,他还梦到有一天去医院检查肛门。但接诊的不是他之前去的男医生,而是一个样貌艳美、言语间充满挑逗的女医生。女医生问他是否害羞,他支支吾吾。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奇怪的梦呢?可能是从一封邮件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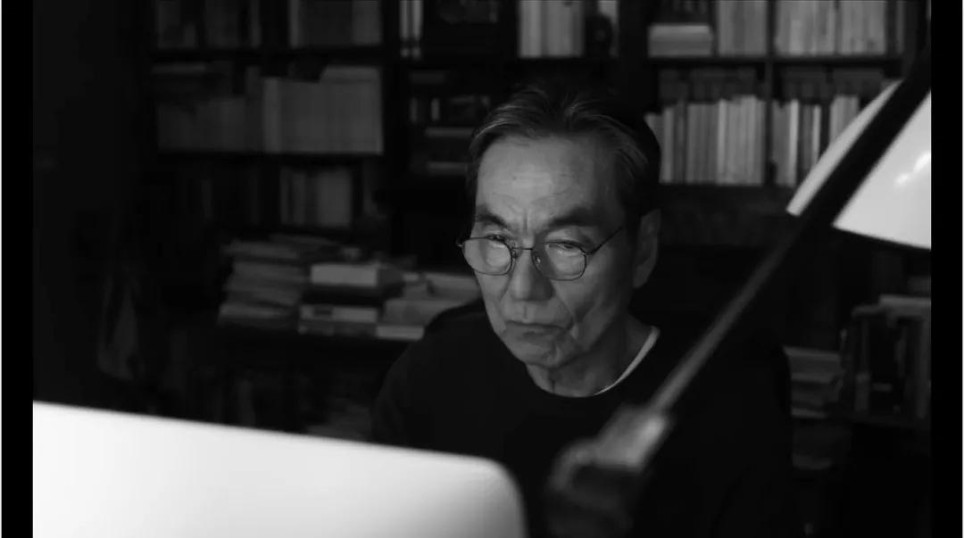
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一封邮件,标题是敌人来了。他好奇地点开看了看。他收到这封邮件之前,刚好因为肛门破裂去医院看了医生。他第二次收到类似的邮件,是自己在杂志连载的文章被告知要暂定了之后。两次收到邮件,一次是在身体出现问题之后,一次是在经济来源被切断之后。
身体抱恙与囊中羞涩,的确是此刻的他之大敌。作为一个文学教授,如此巧合的事件,他不可能不去联想。
如果从现实角度更理智地分析,他可能只是点开了一个钓鱼邮件。此前,他也收过不少垃圾邮件,但多数都是中奖通知。这种邮件他一般看下标题,就直接丢进垃圾箱了。而“敌人来了”的邮件,让他好奇。他点开了一次,钓鱼方就继续发了一次,他又点开了。钓鱼方当然就把他当做目标。在冬的段落里,有一天,他再次收到同样的邮件,但是这次没有内容,只是一个链接。他一点开链接,电脑就黑屏了,再之后就是满屏的乱码。显然,这是电脑中毒了。
冬
冬的部分是电影的高潮,揭示了男主的精神状态已经到了现实与虚幻不分的地步,他的生命日渐走向了终点。
与秋的段落中单事件后确认现实场景不同,在冬的段落中,现实、梦境与幻想的交织更为复杂,而且,事件与事件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关联,因此,对于现实的确认也稍显困难。不过,通过对导演镜头的捕捉,还是可以分出一二。电影中,几位女性角色的出现,可以很好地帮助理解故事的虚实。
一是女大学生的线索。
女大学生是在秋的场景中首次出现的。当时,男主和老友去酒吧喝酒,女大学生是酒吧老板的侄女,她看上去热爱法国文学,很是崇拜男主,主动提出要向男主请教学习。后来,男主也经常来酒吧与女大学生交流。可是,突然间,酒吧关门了,他再也联系不上这个女大学生。
他去医院看望术后昏迷的老友。他第一次跟别人坦陈,自己被骗了。女大学生谎称自己的父亲失业,她无法继续读书。于是,他借给了女大学生一大笔学费和生活费。老友听到这里,很是激动。男主拿开他嘴巴上的氧气罩,听到老友说了句,快跑。眼看着老友即将一命呜呼,男主赶紧去找医生。结果跑着跑着,发现了存放妻子尸体的房间。
梦醒了,他起床继续写自己的遗嘱。

在这个场景中,哪里为真呢?
此前,男主的老友说过要去体检。当时,男主还说,体检是没用的。所以,男主看望老友这个片段,可能是现实在梦里的投射。但不排除他也真的有去看过住院的老友。至于老友让他赶快逃跑,我倾向认为这是梦中的自我加工。在他波澜不惊的生活里,这封邮件难得的挑起了他的好奇。在梦中,将现实收到的邮件内容变成老友的叮嘱,这是有极大可能的。而他看到妻子的房间,很显然只能是梦境。
他的这次惊醒是在半夜里。他写完遗嘱已经很晚了。他饿了,泡了盒方便面。一回头,竟然在院子里瞥见人影,吓得赶紧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但是,这也可能是他的幻觉。或许是窗外的落叶让他误认为有人。在夏的片段里,有个年轻人跟他说过,外面好像有人。这句话,他记在了心里。

二是妻子的线索。
男主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电影中她的出现只有男主的梦境和幻想两种可能。电影中有个镜头交代,有一天他收拾衣物时看到妻子的大衣,就把它挂在了自己的书房里。他有时候会对着这件大衣说话。
还是梦到妻子的同一个晚上,他边写遗书边对着这件大衣说,遗嘱究竟要写到多详细呢?之后,镜头切到他躺在沙发上。妻子从外面回来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对妻子说,他应该听她的话,把这个房子卖掉,换成公寓的。他自己未曾谋面的祖父一直在看着这里。他希望妻子也搬回来一起住。他还说,现在世道不一样了,过去的大学教授的骄傲和自尊,都成了生存的累赘。他现在不愿意为了苟活而活着。但妻子只是不理他,径直走向床上躺下了,说自己累了。
妻子回来的这一段,又是梦。男主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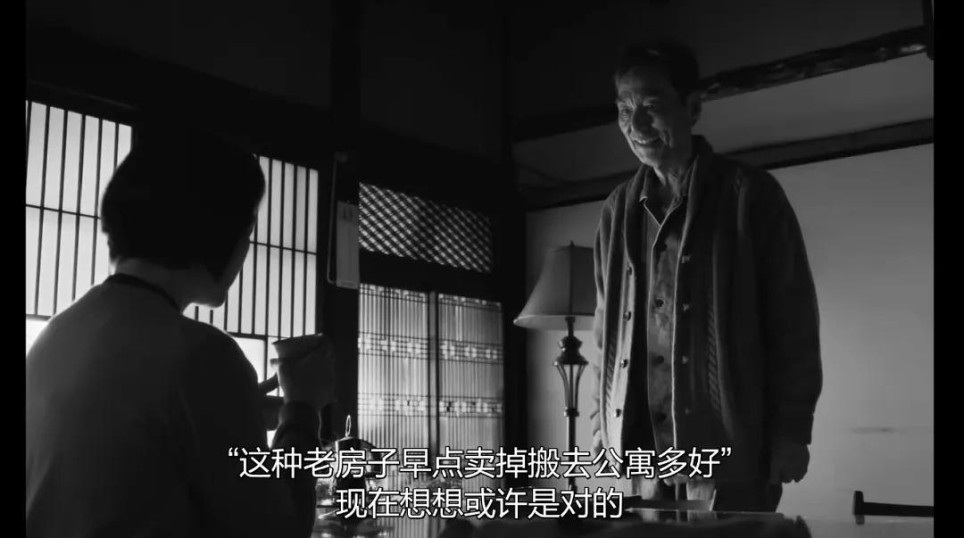
醒来的男主继续处理纸质的遗书。在如常收拾衣物的时候,他发现一条缎带。他试图用这条缎带自杀。终于还是在最后一刻挣脱了出来。
自杀未遂,但他的精神状态是越来越差了。他总是觉得院子里有人。他甚至故意把之前囤的肥皂放在院子里,让人自取,想要看看这个院子里的“敌人”究竟是谁。他总是“看到”妻子。他在淋浴的时候,看到妻子待在浴缸。他也进入浴缸,与妻子说话。妻子有点埋怨他从来没有带她去过巴黎。妻子还叮嘱他,绝对不能和别人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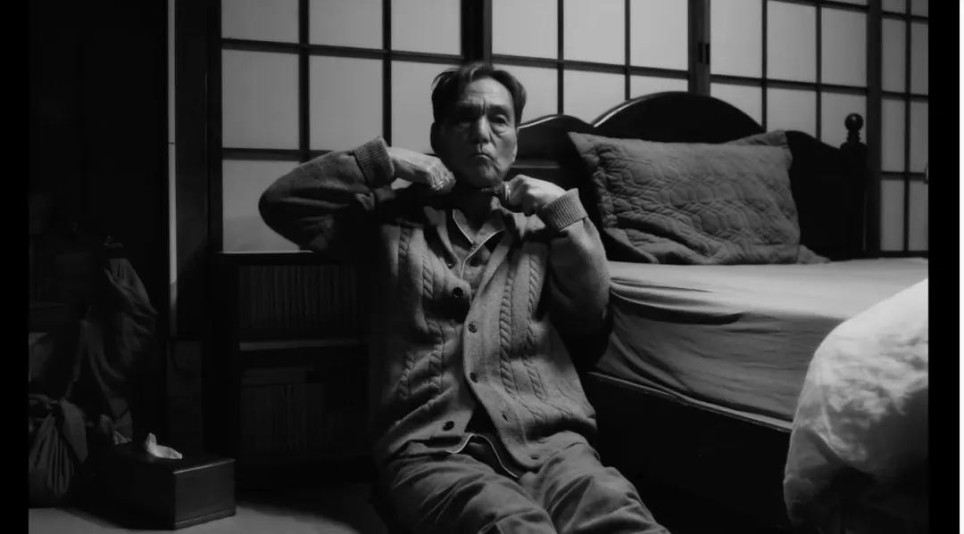
三是女学生的线索。
在冬的片段里,女学生又来了。这次,他们一起做火锅。刚准备用餐时,上次来家里说要暂停男主连载作品的报社小伙也过来了,他说他可以让杂志恢复男主的连载。他闻到火锅香,似乎想要一起吃饭。在此之后的叙事,似乎也是电影中最复杂、最难以理解的一段。
此时,男主的幻觉又出现了。他幻想妻子在家,招呼了报社小伙留下来一起吃饭。他还幻想,妻子对在坐的女学生很是不满,认为他和这个女生在调情。不过,饭桌上他们还是谈论了关于男主的连载主题。他说可能是北方威胁之类的。他还用法语说了句,“敌人不会慢慢入侵,只会突然袭击”。女学生翻译了出来。这引起了妻子的更大醋意和埋怨。他不断跟妻子辩解,但妻子还是执意要离开家。
突然,一阵枪声。原来是女学生把报社小伙杀了。她说他袭击了她。于是,男主和女学生把报社小伙拖到院子里,想要丢进井里。但井边站着之前帮他处理井的问题的年轻人说不能投进井里啊,不然就喝不上好喝的茶了。但是,管他呢,报社小伙还是被年轻人丢进了井里。男主还淡淡地说了句,“只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年轻人死了”。
这时,女学生非但不感激她帮忙处理了尸体,还很无情地揭发了他,认为他当年对她学习上的照顾,只不过是在利用职权骚扰她。她还冷冷地问了句,“你真的活的安心吗?”
结果,这又是一场梦。因为醒来,桌子上空空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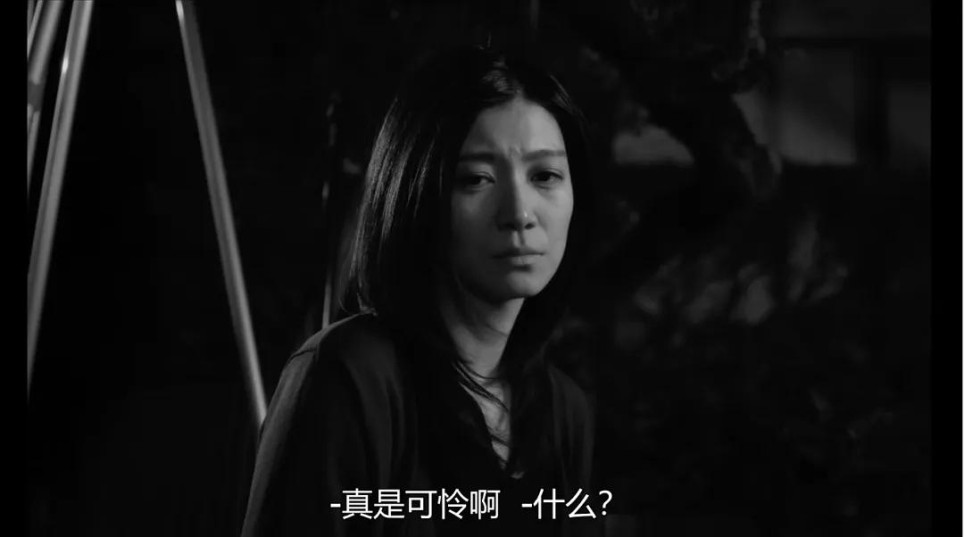
此时是第二天的中午。他的梦应该是午睡的梦。但是昨晚,他的女学生和报社小伙确实过来吃饭了。因为邻居老人说,昨晚他家里很热闹。
那么,报社小伙到底有没有被投入井中呢?
我倾向认为是没有的。这是男主的梦中加工。因为此前,女学生第一次去男主家里,谈到过去时,也谈到她读书时曾被男生骚扰,幸亏那时有男主的帮忙。这段对话和历史,只不过在男主的梦中进行了再加工。

就在男主和邻居老人说话的间隙,在夏的场景中出现过的遛狗女人又出现了。邻居老人和遛狗女人再次因为路上的狗屎而争吵了起来。
此时,男主的幻觉又出现了。(是的,根据男主的精神状态判断,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男主将争吵幻想成了战争。)
在男主的幻觉中,邻居老人被未知的“敌人”杀了,遛狗女人也被杀了。他在炮火连天中跑回家中,找出棍子,想要出去跟敌人拼命,结果自己也中枪了。
镜头切换,男主神情落寞且呆滞地坐在门口,看着窗外下雨。可能是因为他坐着睡着了,轰隆的雷声变成了梦中的战争背景音。

春
春的部分很短,就是一群人坐在男主家中,公证人宣读男主的遗嘱,亲朋好友及遗嘱受益人聆听遗嘱内容。
男主将房子留给了侄子。当侄子在小木屋中找到男主的望远镜,并用望远镜看到站在楼上的男主时,望远镜掉落,电影就结束了。
为什么侄子看到男主就吓得掉落了望远镜呢?我想,应该不是侄子看到了男主的幽灵。可能是,此时的男主已经卧床不起了,侄子很惊讶男主竟然还能够站起来,而此刻的他,其实正在窥视男主的一生。他可能是有一种偷窥者被主人发现的复杂心情吧,不小心掉落了望远镜。
///
最后,回到电影的名字,《敌》。究竟敌在何方?谁是敌呢?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敌人来了”,究竟又有什么深意呢?
这些当然都是开放的问题,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即便是前文的分析,也不能说都是准确的。好的电影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能够引发不同人的不同思考和不同解读。
在电影中,男主的敌,表面上看是日渐走向终点的生命和并不十分充裕的金钱,但在他虚实恍惚的精神内核里,他的敌,似乎无处不在:
他的自尊与骄傲是敌,比如,他不愿意为了金钱而降低自己的演讲酬劳。他说,如果他真的感兴趣,他也可以不要钱就去演讲;
他的体面是敌,比如,他害怕自己身上有老人味,就仔细用肥皂反复清洗自己的身体;再如,他宁愿花费更多金钱和精力,也不愿卖掉房子换成公寓,因为这个大房子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他的不谙世事是敌,比如,他原本出于同情,想要鼓励热爱文学的女大学生继续学业,结果中了人家的圈套,损耗大把金钱;
他的懦弱是敌,比如,他明明愿意也希望能够和自己的女生走到一起,但他始终没有勇气,只能在梦境和幻想中吐露心声;
他的自卑是敌,比如,他从来没有带妻子去过巴黎,其实有个原因是自己的法语并不是很好;他还认为,除了妻子,也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他的虚伪是敌,比如,他身为堂堂大学文学教授,应该对人类充满了怜悯,但他“杀死”了一个年轻人,却冷冰冰地认为那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
这样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是榜样的自律、友善、高尚的人,终其一生,为了维持这份完美的形象,也着实付出了不少代价。 这份“执着”,又何尝不是他的敌。
////
网上不少人在评论这部电影时,会提到另外一部讲述老年单身的日本电影,《完美的日子》。后者在豆瓣的评分更高,可能是因为更文艺。它讲述了一个逃离原生富裕家庭的男子,后来主动选择成为一名清洁工。但他依然热爱读经典的书、听有格调的音乐、拍有艺术的照片,他在看上去卑微的工作和生活中找到了心灵的安定与生命的宁静。
相较而言,《敌》当然是更现实,也更残酷的。《完美的日子》里的主人公,只是还没有走到生命的尽头而已。
生命的尾声,没有体面,没有浪漫。太多人的生命尽头,只是老残零落,一片凋敝。
就像邻居老人和遛狗女人争论的那片狗屎,不管它是大是小,是什么狗拉的,都没人愿意捡起来。
欢迎关注个人公号:非正式文艺杂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相关阅读
 上班下班的一点点心得学习
上班下班的一点点心得学习
 父权与语言的之后是什么?
父权与语言的之后是什么?
 普遍性的吸血鬼
普遍性的吸血鬼
 从第一人称出发能看见种族吗?
从第一人称出发能看见种族吗?
 白发如雪,情根深种:新加坡版《塞外奇侠》的永恒武侠记忆
白发如雪,情根深种:新加坡版《塞外奇侠》的永恒武侠记忆
 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本该做什么都能成功的
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本该做什么都能成功的
 《行尸走肉:达里尔·迪克森》S3E7:远离家乡
《行尸走肉:达里尔·迪克森》S3E7:远离家乡
 躁动与青春
躁动与青春
 霓虹下的生存与救赎
霓虹下的生存与救赎
 原来你也是爱情小丑
原来你也是爱情小丑
 《命悬一生》:原生家庭伤害的救赎,2个邻村女孩因为1点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命悬一生》:原生家庭伤害的救赎,2个邻村女孩因为1点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一部后劲很足的三人行电影——《福冈》
一部后劲很足的三人行电影——《福冈》
 不要被冬天困住
不要被冬天困住
 命悬一生让人绝望地哭,心如刀绞地哭,窒息地哭……
命悬一生让人绝望地哭,心如刀绞地哭,窒息地哭……
 女性是一种处境
女性是一种处境
 破的是心灵中的地狱
破的是心灵中的地狱
 杰出公民|诺奖获得者的获奖感言都说些啥
杰出公民|诺奖获得者的获奖感言都说些啥
 李炳渊还算真诚和努力,但也只剩真诚和努力了
李炳渊还算真诚和努力,但也只剩真诚和努力了
 没有真实 谈何山河
没有真实 谈何山河
 电子影像与游戏体验的媒介互动
电子影像与游戏体验的媒介互动
